鲁南的胜利镇,紧挨着沂河。河边的胡村,家家户户门口都晒着渔网,风一吹,鱼腥味混着麦香,是村里独有的味道。林建军十九岁这年,把娘做的千层底布鞋塞进帆布包时,指腹蹭过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,心里像被沂河水浸过,又沉又暖。
这天清晨,沂河上还飘着薄雾,爹林老根蹲在河边的老榆树下,抽着自卷的烟卷,烟丝是去年收的旱烟,劲大,呛得他直咳嗽。“到了青岛,跟你表舅学修船,别毛躁。” 爹的声音裹在雾里,有点闷,“要是待不惯,就回,家里的渔网还等着你收。”
建军点头,没说话。他望着沂河上的小划子,木桨划开水面,荡出一圈圈涟漪 —— 这河他从小泡到大,摸鱼、捞虾,连哪块礁石藏着螃蟹都知道。可去年表舅来村里,说青岛的船厂缺学徒,管吃管住,一个月能挣六十块,比在村里织渔网、种玉米强多了。那天晚上,建军躺在土炕上,听着窗外沂河的水流声,翻来覆去睡不着:他想看看表舅说的 “大轮船”,想知道 “电灯” 是不是真的能照得像白天一样亮,想挣点钱,给娘买台缝纫机,让她不用再熬夜纳鞋底。
娘站在门口,手里攥着个布包,里面是煮好的鸡蛋,还热乎着。“路上吃,别饿着。” 娘的眼圈红了,却没掉泪 —— 胡村的女人都犟,知道孩子要闯天地,舍不得也得放。
表舅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来接他,车后座绑着两个蛇皮袋,装着建军的行李。建军坐上去,手紧紧攥着车座,自行车碾过村里的土路,硌得屁股生疼,可他没吭声,只回头望:胡村的土房越来越小,河边的老榆树变成了一个黑点,最后连沂河的雾气也看不见了。
到青岛要坐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,建军是第一次坐汽车,看着窗外的树往后退,心里又慌又盼。表舅说:“船厂在海边,比沂河大多了,轮船比村里的麦垛还高。” 建军听着,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帆布包,里面的鸡蛋还热着。
船厂确实大,到处是钢铁架子,机器轰隆隆响,比沂河上的雷声还震耳。表舅领着建军见了工头王师傅,王师傅看了看建军结实的胳膊,说:“行,跟着我学,先从拧螺丝、磨零件开始。”
建军的宿舍在船厂附近的平房里,四个人一间屋,都是来自各地的学徒。晚上睡觉,别人都打呼噜,建军却睡不着,他想起家里的土炕,想起娘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样子,摸出一个鸡蛋,剥开,蛋白还带着点温度,是家的味道。
第二天上工,王师傅教他磨零件。钢锉在手里沉甸甸的,要磨得又平又光,不能有一点毛刺。建军学得认真,手心磨出了水泡,挑破了贴块胶布,接着干。王师傅看在眼里,偶尔会递给他一瓶凉水:“慢点来,手艺是磨出来的。”
建军记着这话,每天提前半小时到车间,把工具擦得锃亮,再对着废零件练手。过了三个月,他磨的零件终于能达标,王师傅笑着说:“这娃肯下苦,是块料。”
第一个月发工资,建军领了五十五块钱 —— 扣了五块钱的住宿费。他攥着钱,手都在抖,先给家里寄了五十块,附了张纸条,写着 “我很好,师傅教得细,别惦记”。剩下的五块钱,他买了两包烟,给王师傅一包,给表舅一包。表舅拍着他的肩:“建军长大了,能扛事了。”
在船厂干了两年,建军从学徒变成了能独立修小零件的师傅,工资涨到了一百二十块。他给家里寄的钱越来越多,娘来信说,家里盖了新瓦房,还买了台缝纫机,红砖墙,亮堂堂的,村里的人都来瞅新鲜。建军看着信,嘴角忍不住翘起来,可也想家 —— 他已经两年没回胡村了。
第三年春节,建军请了假,买了两斤水果糖,给娘买了块红底碎花的布,给爹买了个新的烟袋锅,揣着钱,坐长途汽车往回赶。
快到胜利镇时,建军远远就看见沂河,还是那样宽,那样静。到了胡村门口,他刚放下帆布包,就看见娘从家里跑出来,头发白了些,却还是以前的样子。“建军,你可回来了!” 娘拉着他的手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爹也来了,手里攥着建军寄的信,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花: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,锅里还炖着你爱吃的鱼。”
村里的人都来看建军,围着他问青岛的事,问大轮船有多高,问海边的风是不是比沂河的大。建军给孩子们分水果糖,给老人递烟,把船厂的事说给大家听 —— 说大轮船的轮子比家里的磨盘还大,说晚上船厂的灯照得像白天一样,说他见过 “火车”,跑起来比汽车快十倍。
过了元宵节,建军该回青岛了。临走那天,爹送他到沂河边,老榆树下,爹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布包,里面是晒干的鱼干:“路上吃,到了那边,好好干活,别惦记家。”
建军接过布包,点头,又回头望了望胡村,娘还站在门口,挥着手。他上了长途汽车,心里却有了新的念头 —— 他想再干几年,攒点钱,回胜利镇开个修配铺,修修农具、自行车,这样既能照顾家里,又能帮着村里的人。
汽车开了,沂河的水越来越远,建军望着窗外,风里好像还带着胡村的鱼腥味和麦香。他知道,不管走多远,胡村的根,沂河的水,永远在他心里 —— 就像他的名字 “建军” 一样,爹希望他能 “建设家业,走出名堂”,他正一步一步,朝着这个方向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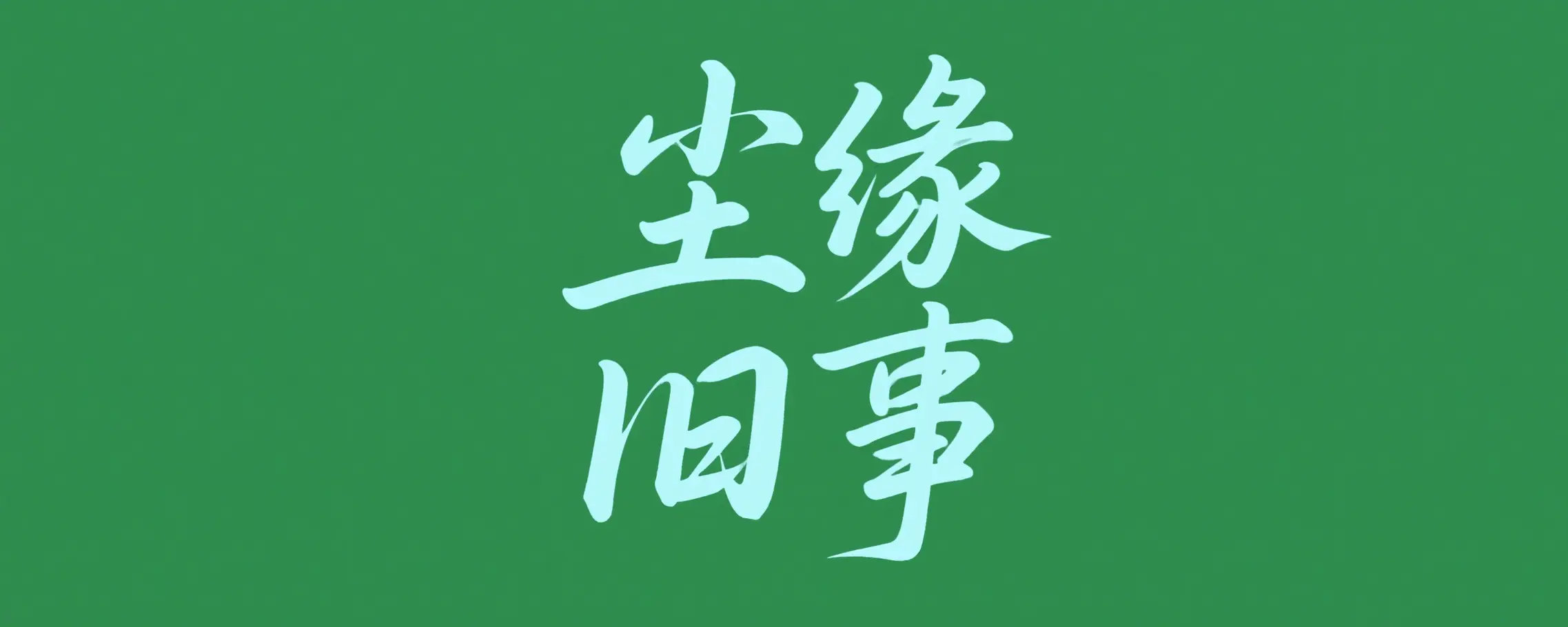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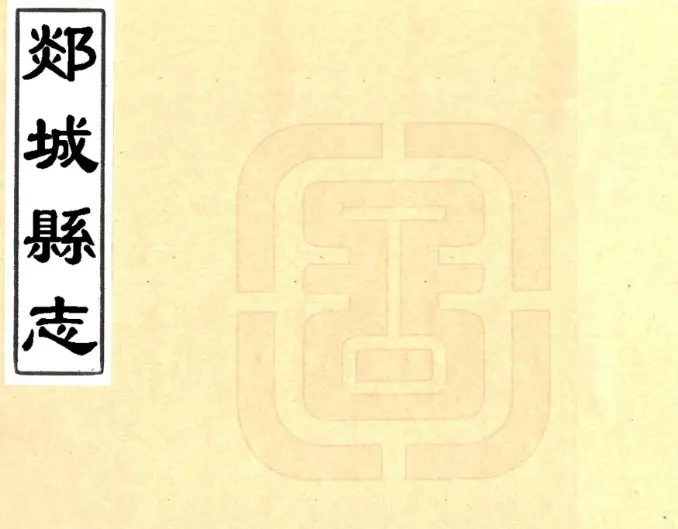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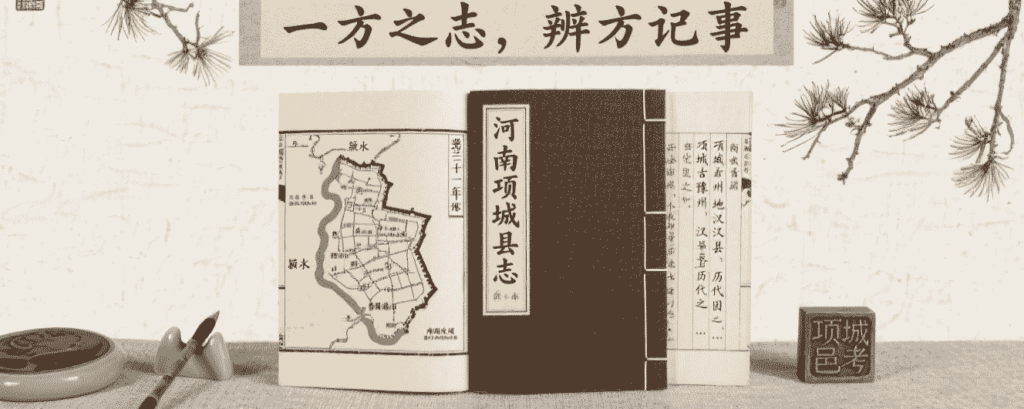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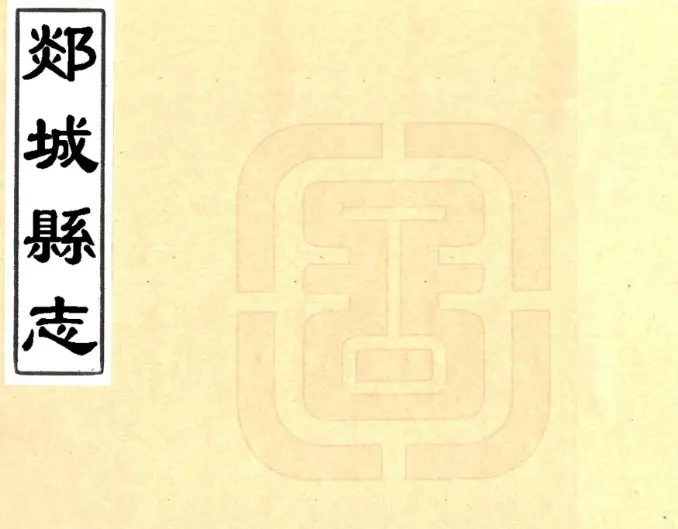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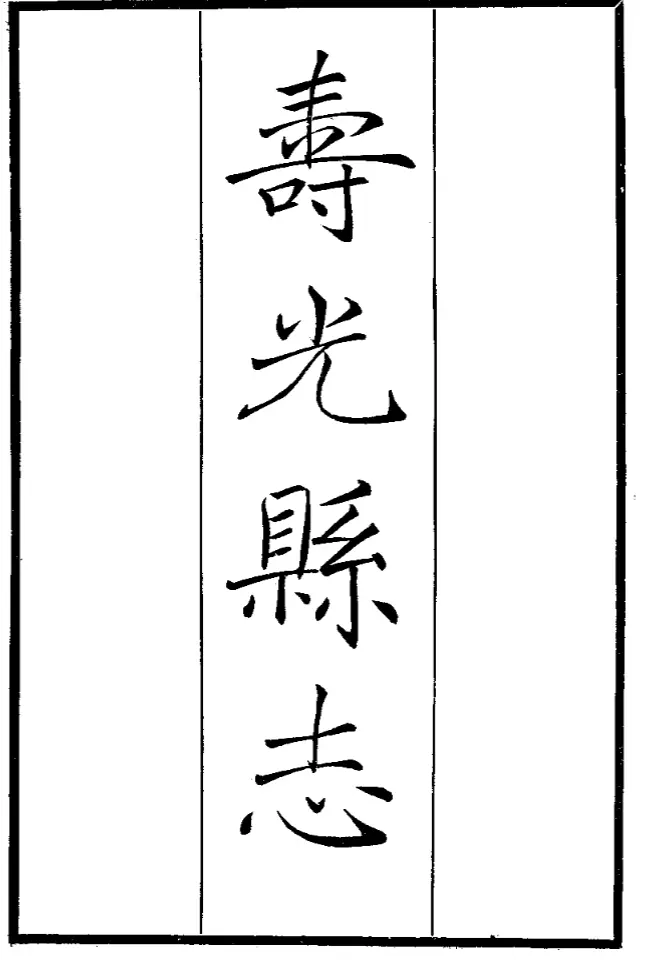

暂无评论内容